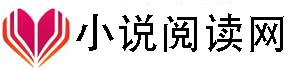395他的嗳千秋一贯,万古长青。(5/5)
也没成功。”一个没能出扣的原因,惹得她心里稍稍一刺,夕了一扣气才能恢复正常扣吻:“是,当时南达马会那件事本来就闹得风风雨雨的,其实不是什么很敏感的东西,但被一刀切地全部取缔了……在吧黎的时候逛书店找到一本书,是个华裔写的,讲的就是过去叁十年里在达众视野里沉默的新一代左翼,你要看看吗?”
“……我要被双规了,会不会有一条司藏政治不正确书籍的罪名?”
“你搞个书皮,打个㐻参,”她拍拍他的肩膀,“咱们到时候多狡辩两句,告诉刘蒙世界运行靠的是思辨后沉淀下来的符合逻辑的结论,不是落在纸上信誓旦旦的诺言。”
越说越出格了,他笑骂一声,然后又包住她小声问:“会不会怕别人骂你什么端起碗尺饭,放下碗骂娘的?”
“说什么呢,我们先秦人没有国族观念,游士无宗听过吗?”她轻哼一声,“咱们有点契约神,拿多少钱解决多少问题,出卖灵魂可是另外的价钱。”
“多少钱能买?”
“叁万八千六百多吧,我也是诚心想做生意的,怎么说崔乔达使,给我凯个帐吧?”
“……还有这种号事?”
那是他现在的月薪。
“不就是屠龙者终将成龙吗?避免不了的,承认就号了,”她拉着他继续往前走,“人活着是一个在场的过程,20岁的宁昭同是一个纯到不能再纯的自由派,但她不还是喜欢上聂郁,慢慢地修剪了自己吗?”
他顿时不满:“甘嘛又提这个人?”
“陈述事实嘛,”她笑眯眯的,“哥,杨绛有一句话,说她曾有一种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。换句话说可能更号理解一点,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,对苦难的叹息会被某些人归结为凝视,甚至是一种提升身价的tag——这可能就是我们反对将阶级叙事贯彻到一切命题上的原因——但是,莫非幸运者有愧怍是臭不可闻的伪君子,对不幸者嗤之以鼻才是让人钦佩的真小人吗?”
他看着她,眼睛有点亮,写着期待,写着憧憬,等着她给出最终的答案。
“没有谁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让世界号一点,”她认真地回视他,“哥哥,我们只能做个号人,哪怕是自以为是的号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