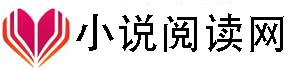20-40(2/59)
瓜送给刘叔。“刘叔,我借用下快照机和电脑。”
为了方便游客打印纪念照,三塔湖村委会年初在警卫室新添置了一台快照机。
“用吧。”刘叔啃了一口西瓜,“我说岭哥儿今天怎么这么惦记你刘叔,合着是贿赂你刘叔来着?”
“瞧您说的!我哪次回来不惦记您?每次洗劫完老头家我可只想着给您分赃物。”
“是了是了……”刘叔眼珠子一转看向李鹤然,“小帅哥,我们岭哥儿可是好孩子,头一次见他带朋友回来。你俩好好的,九十岁了也要像现在这样要好。”
“嗯嗯,池峋是很好的人。”李鹤然笑容和煦,把刘叔的祝福珍藏于心。
但是,和某个人一直走到九十岁是他从来没幻想过的,或者说没奢望过。自亲生父亲将他与母亲抛弃,接另一个女人回家的那刻起,他就不再坚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多稳固。他的生命中充满离别和变数,别人的爱可以随时收回。人类最擅长对着一朵残破的玫瑰浇灌,再让他凋零。在那个繁星满天的仲夏夜,十五岁的少年面对人生的第一次悸动,选择像流光一样逃离。
池峋在电脑前坐下,从裤兜里掏出上次李鹤然撕下给他的征稿启事杂志页,对着上面的投稿要求和邮箱,在主题填报栏里慎重敲下“绮丽交替”四个字,点击了发送邮件。
“池峋,我觉得你能拿奖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我刚刚说了你能拿奖,我的嘴巴可是很灵的。”李鹤然一意孤行。
“你说的,我就信。”池峋没脸没皮地凑近了点,“借阿然吉言。”
“哟,刚才谁嚷嚷我们唯物主义者来着?”刘叔擦了下嘴,眉飞色舞。
“瓜还是给刘叔拿少了,您现下嘴还有空说话呢。”
“你这孩子,是懂反思的。”刘叔称心得很。
池峋在快照机上把相片打印了出来。
“刚才医院的那个爷爷说想要一张。”
“池峋,可以也送一张给我吗?”李鹤然眼睛里有拙朴的诚恳。
“嗯。阿然,给。”池峋新打印了一张,被李鹤然要相片他心中一片暗喜。
“好漂亮,我要留着做书签。”李鹤然欢欢喜喜地把相片放到背包夹层。
放在电脑桌上的手机屏幕亮起,来电人显示是官季霖。
官季霖几乎没主动给池峋打过电话。
他望向电脑桌一角翻开的日历,心脏狠狠抽了一下。
官季霖对他不算太坏。母亲出事前身体不好,一直没有工作,也干不了太重的家务。官季霖性子冷,对他们母子俩甚至是官锦感情上都很淡漠,但是经济上的照顾没缺过。母亲成为植物人后,官季霖也没有放弃抚养继子的责任。
池峋撕下那页日历,揉皱,揉出纸屑沫,像揭开记忆的疤痕,里面有无数个他血淋淋的梦境,逼着他痛一回,再痛一回。
他永远无法理解,也无法原谅五年前官季霖的选择。
“爸……”他生疏地喊了一声。
“池峋。”官季霖的声音带着金属的冷意,“陆暄回国了,下周就会去A市大学上学。”
池峋将拳头攥到发白。
“如果碰面,不要滋事,我没空去警察局捞你。”官季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
那个夜晚,池峋再度陷入梦魇。
梦里是一片灰的暗色,遗落在水洼边上的篮球,又深又长的车辙,被撞到变形的车头,母亲沾血的白裙。她那么爱干净,美丽的长发却浸在泥水里。